两个放生小故事
发布时间:2023-09-24 05:23:46作者:金刚经修行网故事1: 2003年年初,正月十五,北京组织了一次很大的放生,邀请我的师父主持。放生的金额我记得大概有十来万,在颐和园的南门外的引水渠,参加放生的人大概有四五百人,或许是因为我的师父有些名气,有不少人甚至是从外地专门赶来参加的。放生的动物主要有鲤鱼、泥鳅、龟鳖和鸟。放生从上午10点开始,热热闹闹的持续到大约12点左右结束。大约是看出了什么,我的师父走时交代我们一些弟子先不要走,留到下午。师父走了,人群逐渐散去,可除了我们大约20多个年轻居士在留守外,渠的对岸,桥上,冰面上还站着不少人。仔细一看,应该都是当地的居民,还有一些地痞流氓。噢,我这才明白过来,原来让我们留守是为了防止他们捕捞呀。再一看,很多人手里拿的都是长达4米的扎杆,专业的捞子,我们呢?只有一两根歪歪扭扭的树枝,长不过1米5。这可惨了,当时是冬天,除了我们放生的那一块水面因为留给人冬泳的原因没有上冻,只有40平方米左右,其余的水面上都结满了冰。连活泼好动的泥鳅放下去以后都冻晕在水底,更不用说别的鱼和龟鳖,一眼望去,水下密密麻麻全是一动不动的活物。我们也不敢吃饭,就死守着,流氓们是最先围上来的,开始抄水面上的鱼。我们和他们还有了冲突,甚至本人还冒充一下便衣警察吓唬他们(现在想来真是胡闹)。下午两点,冬泳的大爷们来了,扑通跳进水里,上来就骂,说我们虚伪,放生还是放死,水下白花花全是不动的鱼,好像说还有巴西龟(热带龟放到北京寒冬的冰水里,倒也是巴西龟史里独一无二的生存挑战)。冬天黑的快,到了傍晚,留守的也就成了我们七八个了,而对岸的居民已经是乌泱泱一大片。我们在整个过程里一秒都没有闲过,想尽办法不停的用树枝把一条条鱼和泥鳅往稍远点的水面下拨,感觉似乎只要视线里看不到,它们就能安全,其实自己也知道是自我安慰。后来实在没办法了,只好又开始往回捞,鱼和泥鳅没办法了,只能抢救甲鱼,想办法终于捞回了10来只,可放下去的有几百只。带着这几只甲鱼,我们天黑时离开了,侥幸的想或许天黑他们看不见会捞不着。其实40平方米的水面下屯积着10多万元的鱼,颐和园公园的水闸也不开,闭着眼睛直接抄就是了。走时还碰到有些当地的小孩正在玩弄爸爸给他抓的小鸟,我们去理论,就又被村民围了起来...。 事后,大概是向我的师父反映不满的人很多,所以当我也向他表达对这次放生的看法的时候,他马上打断我说这次放生还是很圆满的。既然师父都说了,我当时也就心下释然了。一两年之后,当自己对佛法的闻思又多少增进了一些后,我才明白过来,当时他说圆满其实也应该是无奈的安定民心之语,因为在之后的几年放生里,他再没有让当时组织放生的人再去承担放生主要组织者的任务。又两三年之后,也就是在我现在看来,虽然由我的师父个人组织的放生在之后的几年里的确得到了很大的改善,但我想如果至少问责制在当年如果能实行,那该多好!故事2: 2005年,还是正月十五,五明佛学院的一位在汉地很有名声的堪布在北京组织放生,地点在房山的青龙湖公园,距市区很远,湖面上依旧结着冰。放生时很好,大家也有秩序,各司其责,我想这跟这位堪布一向严谨的作风有关。放生完了,堪布先走了,大家接着慢慢离去。当我们刚走出公园大门的时候,突然有道友接到还在湖边的人的电话,说当地的村民来了好多辆车,开始捕捞。我们大约20来个年轻的居士马上往回跑,赶到湖边一看,可不是嘛,正往车上装呢!我们赶紧上前,把他们手中的麻袋往下夺,冲突不可避免,我夺了两个人手里的袋子后,发现有一辆夏利要开走,我想里面可能有鱼,于是两步跑到了车前,这是在我身前已经有一位女居士拦在车前。司机看我们要拦他,开始加油门,我身前的女居士也就让开了,我心想,要让你跑了,鱼怎么办?于是我一动不动的站着,这是一场意志的较量,司机也不减速,笔直朝我冲过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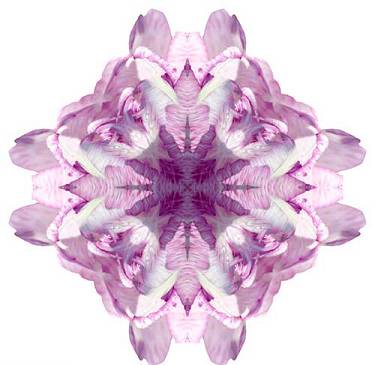
(稿源:佛字人旁-正心堂的BLOG)



